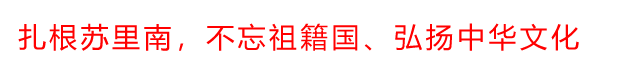三叔的婚礼 - 李民增
| 来源:作者投稿 | 发布时间:2016/9/28 |
三叔的婚礼就是葬礼。不明白吗?听我慢慢说。
他是我老家院中的三叔。在我的记忆中,他个不高,光头,高颧骨,大眼睛,窄眉头,尖下巴,黑瘦。冬天穿件破棉袄,夏天光脊梁,不穿鞋。很少见他穿件像样的衣裳。
他好脾气。生产队的时候,社员们一块干活。地头休息时,年轻人都爱跟他坐在一起,跟他闹着玩。偶尔动手摸他的头,他只是笑着躲一躲,或者用手挡一下,说声“憨样子的,闹么?”从来不恼。
三叔有两个尽人皆知的口语。本地方言,把“去”说成“气”,他说“趣”,后边还有一个长长的拖音。“三叔,赶集去不?”“趣——”他就这样回答,很有特色。小青年们都好学他。还有一句,“那咱脑”。不管别人说什么,都是回答“那咱脑”,意思是:“对,就是你说的那样。”不抬杠,更没跟谁红过脸。
二叔很精明,看见青年们跟三叔闹得过分,就正颜厉色地说一句:“您给憨子闹么?”闹的人脸一红,便不好意思闹了。
三叔可不憨,就是老实。庄稼活样样精通,又听话,队长叫干么干么,是我们队里公认的好社员。他干集体的活认真,给乡亲们帮忙也上心,人缘特好。不论谁家有事,脱坯打墙,泥房盖屋,还有耩地扬场什么的,都是一叫就到,饭孬好不在乎,干完活回自己家吃也行。他的理论是:“谁家该没点事哎!”
三叔什么都好,就是命不好。父亲去世早,两个哥哥成家自立门户后,他与娘在一起过了些年。娘去世后,他就一个人住在小西屋里,不像个家样,过年也不好好打扫整理一下。
大年初一我去给他拜年时,看到他屋里黑洞洞的,没下脚的地方,就在门口喊:“三叔——!来给你拜年哩!你过年好啊!”
他就赶忙走出来,堵在屋门口:“好好!我还没给哥哥、嫂子拜年去哩!”他说的是我父亲、母亲。不叫我进门,我就不勉强,怕他难为情。
他实在是太穷了,赶集只是买一点烟叶,很少见他有买菜的时候。有人说他连老咸菜也不吃,就是蘸点咸水。那时候,人们买不起洋烟,吸烟叶多了也买不起,就掺点儿“葛脑”,就是打场剩下的碎豆叶、绿豆叶之类。三叔是以吸“葛脑”为主,多少掺点儿烟叶。
三叔也有理想与追求。在艰苦的岁月里,三叔像小草一样,不管生活条件多差,都能保持乐观,不怕雨,不惧风,给世界带来绿色,报告着春天,孕育着希望。
一年秋假,我跟社员们下地干活休息的时候,他问我:“民增,人都说‘楼上楼下,电灯电话’,你说咱能熬到那一天不?”
听到我肯定的回答后,他满意地点点头,“嗯”了一声,又笑笑说:“还有这推碾子推磨,以后也不知道有好法不?我不怕下地干活,就怕推磨,跟驴一样围着磨道一圈一圈地转,晕。”
我告诉他:“以后有电磨。下地干活的时候,扛着点粮食,放在村头磨坊里,下地回来,就能扛着面回家做饭。”别人都笑,不信;他信:“那可好了!我还赶上了呗?”“赶上了!”我说,“很快。只要拉上电,马上就能用上电磨。”
后来不仅推磨问题解决了,温饱问题也解决了。可惜他没赶上。
三叔一辈子单身,到老才娶了一个媳妇,年轻漂亮,与画上的美女一模一样,跟他不离不弃,只是不会说话,没感情。那是他去世后,侄子请人剪了跟他陪葬的纸人。
他是我老家院中的三叔。在我的记忆中,他个不高,光头,高颧骨,大眼睛,窄眉头,尖下巴,黑瘦。冬天穿件破棉袄,夏天光脊梁,不穿鞋。很少见他穿件像样的衣裳。
他好脾气。生产队的时候,社员们一块干活。地头休息时,年轻人都爱跟他坐在一起,跟他闹着玩。偶尔动手摸他的头,他只是笑着躲一躲,或者用手挡一下,说声“憨样子的,闹么?”从来不恼。
三叔有两个尽人皆知的口语。本地方言,把“去”说成“气”,他说“趣”,后边还有一个长长的拖音。“三叔,赶集去不?”“趣——”他就这样回答,很有特色。小青年们都好学他。还有一句,“那咱脑”。不管别人说什么,都是回答“那咱脑”,意思是:“对,就是你说的那样。”不抬杠,更没跟谁红过脸。
二叔很精明,看见青年们跟三叔闹得过分,就正颜厉色地说一句:“您给憨子闹么?”闹的人脸一红,便不好意思闹了。
三叔可不憨,就是老实。庄稼活样样精通,又听话,队长叫干么干么,是我们队里公认的好社员。他干集体的活认真,给乡亲们帮忙也上心,人缘特好。不论谁家有事,脱坯打墙,泥房盖屋,还有耩地扬场什么的,都是一叫就到,饭孬好不在乎,干完活回自己家吃也行。他的理论是:“谁家该没点事哎!”
三叔什么都好,就是命不好。父亲去世早,两个哥哥成家自立门户后,他与娘在一起过了些年。娘去世后,他就一个人住在小西屋里,不像个家样,过年也不好好打扫整理一下。
大年初一我去给他拜年时,看到他屋里黑洞洞的,没下脚的地方,就在门口喊:“三叔——!来给你拜年哩!你过年好啊!”
他就赶忙走出来,堵在屋门口:“好好!我还没给哥哥、嫂子拜年去哩!”他说的是我父亲、母亲。不叫我进门,我就不勉强,怕他难为情。
他实在是太穷了,赶集只是买一点烟叶,很少见他有买菜的时候。有人说他连老咸菜也不吃,就是蘸点咸水。那时候,人们买不起洋烟,吸烟叶多了也买不起,就掺点儿“葛脑”,就是打场剩下的碎豆叶、绿豆叶之类。三叔是以吸“葛脑”为主,多少掺点儿烟叶。
三叔也有理想与追求。在艰苦的岁月里,三叔像小草一样,不管生活条件多差,都能保持乐观,不怕雨,不惧风,给世界带来绿色,报告着春天,孕育着希望。
一年秋假,我跟社员们下地干活休息的时候,他问我:“民增,人都说‘楼上楼下,电灯电话’,你说咱能熬到那一天不?”
听到我肯定的回答后,他满意地点点头,“嗯”了一声,又笑笑说:“还有这推碾子推磨,以后也不知道有好法不?我不怕下地干活,就怕推磨,跟驴一样围着磨道一圈一圈地转,晕。”
我告诉他:“以后有电磨。下地干活的时候,扛着点粮食,放在村头磨坊里,下地回来,就能扛着面回家做饭。”别人都笑,不信;他信:“那可好了!我还赶上了呗?”“赶上了!”我说,“很快。只要拉上电,马上就能用上电磨。”
后来不仅推磨问题解决了,温饱问题也解决了。可惜他没赶上。
三叔一辈子单身,到老才娶了一个媳妇,年轻漂亮,与画上的美女一模一样,跟他不离不弃,只是不会说话,没感情。那是他去世后,侄子请人剪了跟他陪葬的纸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