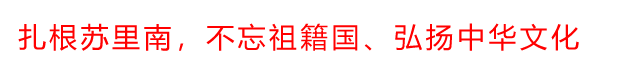该放的放下,当拿的拿起 —— 文/姚信成
| 来源:作者投稿 | 发布时间:2019/12/3 |
我那天一大早就去了县城的新华书店,一头扎进去竟忘了时间的流逝,出来的时候天已擦黑,关键是进店前还是天朗气清而这时却飘着鹅毛大雪,看地上积雪的厚度是下了差不多一整天了,所幸没有错过回去的末班车。然而回到矿区的住处时我却被眼前的景象怔住了:这时候天已全黑,只有茫茫雪海泛着白光,由远及近的两个人影竟是多年未见的四哥和他的小舅子,他受母亲之托不远千里到新疆看我,手里拿的却是一半靠回忆一半凭猜测写的错误地址,歪打正中找到的是我离开一年之久的另一个矿区,让我百感交集的是四哥见面不说自己大雪纷飞中投亲未遇的委屈和艰辛,而是急不可耐地向我赞叹谁谁谁对他们多么多么好,谁谁谁为他们做了什么什么。原来他们一到那个矿区先是被跟我从未正面来往过的经警领他们到了我以前的房东家里,而房东老太则像迎接久违的亲人一样热情接待悉心照顾。找到我们矿上的住处又是跟我打过架尚未和好的室友热情接待做饭给他们吃。
后来的有一年春天,我接父母来兰州过元宵,父母来的时候不巧我出去干活了,同院里住着五六位女房客,她们的个人资料我一无所知,四五年里平均每人跟我搭话不出三五句,有的一句话都没说过,而正是这几位熟悉的陌生人替我接待了我的父母,八九后天我父母回家,母亲拉着她们的手依依不舍千恩万谢,让我深深感动又十分意外。短短几天里这几位素无来往的邻居们给了我母亲无微不至的照料。
2016年我在一家酒店洗碗,有段时间里,每天都有两位美人坯子有空就到洗碗房里帮我洗碗怎么也劝不住。有一阵子我的心境很不好,意识到自己这辈子只怕得孤独终老,早该学会一个人独自面对一切了,凑巧我当时得了场急病需要做个小手术,于是坚辞推掉了要来陪护的家人,包括正被我接在身边的母亲也没去医院,我在医院里各种异样目光的包裹里一个人独自排队办理各种手续,一个人独自排队受检,一个人排队换药,自己高举着输液的吊瓶上厕所。但我拦住了所有亲人却没有拦住帮我洗碗的一位女同事,她先是坚持要到医院去探视我,我说我已经回来了,只是每天去医院换一次药而已,然后她就到了我住的巷子口,我还试图劝她回去,而她一句“你就出来一下吧谁一辈子能没个事呢”就把我的心理防线打了个落花流水。
我的家人受到了我的意外的朋友(之所以意外是因为有些人我们之前素无来往并非常规意义上的朋友)热心关照,而我家人的哥们给我的却是冷遇乃至欺凌。我回家后与同乡们一道外出打工,弟弟先是替我来了一番侮辱性自谦,说我这也不行那也不行,然后多多拜托他的哥们关照一下,而他的这些哥们要么视我为包袱厌恶排挤我要么以为白捡了个私人勤务员连我的人身自由都想控制,有了更好的机会想都不想就抛下我扬长而去;而四哥最铁的哥们在打零工时遇到我居然容不下我,挖空心思想抵制我。
没发现过弟弟的哪个朋友是足以共患难可以托付大事的,但弟弟在村子里很吃得开,我想租个邻居的房子以方便回去照顾年迈的父母,但邻居害怕把房子租给我我弟弟会有想法担心得罪我弟弟竟没敢答应我。
在男人堆里,至少在最初的时间我总是备受排挤,平心而论这并不能全怪别人。小时候意外损失的听力在社交圈里往往会对别人形成无意的伤害,而腼腆木讷的我很少有勇气及时消除误会。寂寞的事业其实也是拒绝社交圈子的打扰的。作为一个农民工,我也许不该误入学术世界,身为学者,我不该同是一个农民工,更不该是一个对公共利益有着与生俱来的强烈责任感农民工,当千军万马挤高考这座独木桥的时候,我只是想学点一技之长以图改变故乡贫穷落后的面貌,而随着年龄的增长这个故乡的概念的外延越来越大直至国家乃至人类。而这一切都是命运的安排,当你发现了别人没有发现的世界的时候你怎么能够停住前进的脚步呢?学者和农民工的身份这样不可兼任,我能化解两个身份的矛盾的办法就是远离社交圈子,作为学者把自己扔在生存底线上本来就是个错误,把打工挣来的菲薄收入花到社交场合呼朋唤友对我是莫大的损失,所以我不能不经常选择相当的抠门,回家的时候我会给父母买点高档水果,但我极少给自己买过什么零食。
其实学者也是一个挺烧钱的职业,光是马恩著作我先后就花了一千多。较之买书,发表论文才是真正烧钱的火坑。版面费本来是国际惯例无可厚非,但中国的病在于毫无原创性的烂稿堂而皇之地登上核心期刊的大雅之堂而且劣币驱逐良币,所以在当下之中国天才的前途捏在庸人的手里的现状就变得再天经地义不过了。有些期刊公开宣称不收版面费的,但投过稿才知道投稿渠道掌握在收费的中介公司手里,在中国期刊遍地开花枪手公司风生水起,受伤的就总是学术的健康发展。
除了必须的牺牲,我在社交上也有自省的必要,人格魅力的修炼是我一生一以贯之的做人准则,“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是我坚如磐石的人生追求,但我忽略了“水至清则无鱼,人至清则无友”,忘了韩信以胸怀雄才大略能忍胯下之辱,宋美龄以第一夫人之尊能忍被美军开除的兵痞流氓的言辞不敬,邓小平以共和国核心领导人之尊忍了三流乃至不上流的部下掀翻的牌桌,但《戈壁母亲》看了很多遍,刘佳演绎的伟大母亲面对针对自己的不平不屑一鸣的大气我却没有学到,《麻辣芳邻》虽然百看不厌但老杨的大度与包容我也没有学到多少。嫉恶如仇虽然使我永葆了满腔正气从不为稻粮随波逐流但也助长了我气量狭窄的弱点,我对自己命运的风雨飘摇其实也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成大事者进入到一个不好的环境,遇到一个不好相处的人,这本是一个磨炼心性的好机会,但我多少次遇到这样机会都遗憾地没能意识到更谈不上珍惜。我像猪八戒一样一遇到挫折和压抑就知道散伙,就知道回高老庄,岂知高老太爷愿意招收猪八戒入赘高老庄的动机也未必是纯的,普天下就没有一块真正的净地。
阴差阳错成了草根学者,我越来越意识到传统意义上的所谓成功的渺茫。在传媒众多的现代社会,作家可以有多种渠道发表作品,只要你有写作的天分只要你精耕细作不懈努力,知名度是可以一点点地撑起来的,而学者的论文发不到指定刊物上你就发也白发。只不过,被压制的真理乃是圈内的当权者埋给自己的地雷,这个真理愈是重要,被压制的时间愈久,引爆后对当权者的杀伤力就愈大,权力的滥用是有成本的。
“苟利家国生死以,岂因祸福趋避之” ,明清两代的作家,他们的作品没人出版,写作的劳动没人支付稿费,但他们还是坚持兢兢业业地写呕心沥血地写。既然我的学说能为人类谋福利,难道没有个人名利的所谓成功就该举步不前了吗?中国历史尤其是文革史被丧失道德底线的王年一(他就是迎合当时中国社会消极情绪大肆卑劣地污蔑)之徒涂抹得面目全非,难道我不该站出来大声疾呼吗?经济学被食洋不化的茅于轼之流(他们就是力图把西方经济学已经摈弃的垃圾强加给中国)搅和成比皇帝的新装搞笑的东西,难道我不该奔走呼号吗?世界共运事业被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演绎成无聊的清谈,难道我不该做点建设性的努力吗?
杜甫号为诗圣,但他的诗作在生前却不为社会所承认,当他突然名声鹊起的时候他已经去世五十年之久了。我忽然觉得,生前寂寞死后成名对我其实就是我最好的结局,我一直都在做一个拒绝社交于千里之外的隐士,我已经习惯了自闭式的生活,如果哪天突然被推到社会舆论的前台了,我真能适应新的生活吗?那是我想要的生活吗?“塞翁失马焉知非福”,没上过大学,我的思维得以避免了专业樊篱的羁绊,读书没有职业学者的功利心,我的思想避免了很多知名学者的贫乏,意气用事频频失业虽然误了钱袋却强了事业,每有重要的读书、写作计划我都特别需要这样的失业机会,村子里谁谁谁盖别墅了谁谁谁买车了谁谁谁盖别墅又买车了跟我没有一毛钱的关系,勿论才情,仅以我的潜在人脉我若刻意求财十之八九能比他们取得更耀眼的成就。但在我的人生历程中求财的欲望总在给事业让道。所幸十四亿分之一的人上无片瓦下无立锥之地毫不影响全体人民不愁吃不愁住,何况我也不愁,生死都已看淡了,吃住问题犯得着愁吗?清贫是我当初的选择,既然选择了就该自己为自己的选择负责,怨天尤人不是男人本色。我已经开始拒绝缴纳医保费,小病没地报大病懒得治,这个世界上只有巴尔扎克列宁鲁迅毛泽东生命多活一分钟就有一分钟的意义,而我冲得再猛也是小兵一个,何况马克思生前有五分之四著作都供老鼠磨牙了,我的绝大部分作品只怕都连供老鼠磨牙的机会都没有。论文发不了我可以化整为零以随笔杂谈类文字到处传播我的思想,当中国学术发展到我的成果的境界的时候会有人想起我曾做过的努力的。不过白说也说是一回事,但生命到了终点还要借助现代医学与规律抗衡,吾不为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