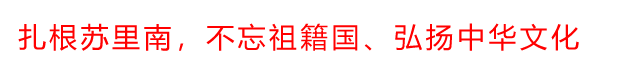我跟严师打交道 (作者:李登祥)
| 发布时间:2018/8/20 | 来源:作者投稿 |
教书十三四年来,我一直以严师的形象跟学生相处,希望他们在我的严格管教下,能够学有所成,至少不虚度宝贵的光阴。我之所以这样做,因为在我走过的岁月里,一直跟严师打交道。其实,说起跟严师打交道,介于我的职业性质,以及教书之余的爱好——喜欢写文章,从来就没有间断过,也就是说,无论过去、现在,还是将来,都将一如既往,他们就像一盏盏明灯,照亮着我前进的道路。现在,他们又在我的脑海里浮现了,始终与我保持着不离不弃的距离。
彭大春老师,算得上是我启蒙的第一位严师。别看她作为聘请的老师,每月只有少得可怜的几十块钱,对教学可认真负责了,远比那些公办教师有过之而不及。她教的是《语文》,就要求我们会读、会背、会默写每课的生字、词语和句子(指她认为的重要句子)。倘若这样,对于记忆力超强的我来说,都是小菜一碟。最头疼的是背《词语手册》,既没有故事情节,又不连贯,没有几人能背得了的。记得有一次,我回家贪玩了,导致第二天下午放学后,我荣幸进入了被关押的名单,一直挨到晚上七点过钟才得以回家。走出教室门,一向自尊心强的我哭了。“我可是经常考前三名的,怎么被关了呢?”我不敢看向彭老师,也不敢看向在门外等我的母亲。我让她们失望了。同时,我暗下决心,从今往后,我一定按时完成老师布置的作业,做一个老师喜欢的学生,母亲眼里的乖孩子。
说起彭老师关押学生,可是出了名的,她干脆不回家了,直接住在学校里。她很生气地说:“我就不信治不了你们!我告诉你们,每天下午放学后都要背诵、默写,完成不了的,就留下来陪我,直到背得为止。”她说到做到,从不在家长的面前有所改变,幸亏那时的家长纯朴得没有怨言,还说她是为了他们的孩子辛苦付出。是的,她为此浪费掉许多时间,通常都要持续到晚上十一点过钟,才在万般无奈之际,挥手让实在背不了的、默写不了的学生随父母回家。当然,也有少数学生——也有可能是家长受不了的,帮忙转学了。我倒是坚持了下来,却不敢再松懈了。就这样,她以严师的形象,一直陪伴着我走过小学六年的时光。我以为随着时间的推移,会渐渐的忘了她,殊不知,我对她的印象越来越深刻,好像不曾离开过。还常常在写文章时发出感叹:“要是当时不遇到这样的老师,我认识的字就没有这么多了。”所以,我在接手《语文》后,除了探索适应时代发展的教学方法外,也在沿袭着当年彭老师潜移默化给我的教学方法。
进入初中后,我的又一位严师出现了——他是我的张华老师。他对我的严格在于:作文题目要标新立异,让人有想读的冲动;内容要情真意切,只有做到发乎心声,才能达到感动人的目的;最好不要有错别字、标点符号的错误,那样会让分数大打折扣。张老师如是鼓励我,说我在《语文》方面有建树,不过,还得加强学习。他说如果我真的想学好《语文》,他可以帮助我。我是一个求知欲极强的人,当时,就点头答应了。其实,不用说当时,就是换作现在,我也会毫不犹豫的答应的,因为没谁愚蠢到在这么好的老师面前,忍心拂他意的地步。张老师很高兴,立刻把我带到他的住处,拿出一本厚厚的作文书给我,说:“拿去看吧!多看几遍,别忙着还我。真的看完了,再来换书吧!我的作文书有很多。对了,你在一边看作文的时候,也可以一边写,写好后拿给我,我会给你修改的。”我再次点了点头,且忍不住说了一声“谢谢”,这是发自内心的。
在前面,我说自己是一个求知欲极强的人,一点也没有夸大其词的成分在里面,自从我得到张老师的重视后,开始了比以前更加爱学习《语文》的征程。时间的天平也跟着倾斜了,导致《语文》成绩是取得了突飞猛进的效果,其他学科却开始出现了严重下滑的倾向,最明显的是《英语》。其实,我除了求知欲极强外,虚荣心也不甘示弱的越居一线,想得更多的是,写出一篇篇的好作文,得到张老师更多的表扬。然而,太多的时候满腔热忱写下的作文,却在张老师那里碰了壁。他不是指出我的作文题目不够吸引人,就是有的语句不通,还有标点符号的错误。更加让我自惭形秽的是他在作文的末尾写上“愚师阅”三个字,不是在嘲笑我吗?我笑了笑,不服输的心让我像发誓似的说:“我有一天会赶上你的。”真正与张老师决裂,那是在读初三的上学期,我参加了由学校负责收集上交到县里面的作文大赛,张老师说我的这篇作文写得很糟糕,最好是重新写。长时间的郁积一旦爆发,犹如雨后山洪。顿时,我没好气地说:“我就不改了,就这样交上去吧!”过后的意外获奖,让我错误的认为,是张老师的眼光出了问题。许多年后我才明白,张老师真正的用心良苦,是为了让我更有机会崭露头角,才如此严格的要求我。
我以为家庭的突发变故(初一下学期的一天,一场大火烧毁了我赖以生存的家),读书生涯会随着初三的结束而结束,却不曾想,父亲(母亲在我十一岁那年离开了人世)咬了咬牙,坚持要送我读职业学校,以期我在三年后摇身一变成为名副其实的乡村教师,端上国家的铁饭碗。也是在父亲的坚持下,我得以在师范三年,有缘认识了我的第三位严师——黄明春老师。他是教《数学》的。说起在关押学生方面,他似乎显得与我之前的两位严师有所不同——不,应该说与彭大春老师有所不同:彭老师关押学生是在下午放学后,而黄老师关押学生是在上午放学后。他往往出几道题,规定做对的就去吃饭,做错的就关一会儿,大概等到做对的学生吃完后,他才放做错的出去。弄得许多做不起题目的学生怨声载道,又不得不默默的接受。我也被他关过一次,说难题都会做了,还用得着做简单的填空、选择题吗?而我在他要求做的过程中粗心大意,把一道选择题选错了。
虽然黄老师只教了我一年,但是,他严格的教风,一直深深的影响着我,让我在不时想起中,觉得很有必要这样要求学生,因为在学生之中,也不凡像我一样眼高手低的。“你说你会做了,就做出来给我看看。只有你做对了,才算得上是真正的懂。”我的每届学生,在与我接触一段时间后,都领教到我的严格之处,所以,他们做到我出一道题,就做一道题的习惯。除外,我还要求他们写好每个字,做到写字如做人。
十二年的时间说长不长,说短也不短,不过,我还是告别了学生时代,结束了依靠父亲生活的日子,开始了自己挣钱养活自己,还赡养父亲的生涯。我有些飘飘然起来。“我是老师啦!我不用再跟老师打交道了,而是倾囊相授给我的学生。”说起我们那一届毕业生,不知道算不算得上幸运的,既遇上了降分扩招的机遇,又不偏不倚的坐上了县里启航的第一艘支教的船。二〇〇四年的九月——二〇〇五年的七月,我在离家只有几分钟路程的云盘小学支教,受到爱好文学创作的我的三哥的影响,开始了写作。然而,我的第一篇得意之作《白云下的儿女》很快就遭到县文联的拒稿,说我写得一点也没有小说的意味。我很不解,难道三年的师范白读了吗?马成宇老师还说我的作文写得不错呢,怎么到了这里就不行了?本来,我想下功夫苦心钻营写作的,但是,想着既要读函授专科,又要自考本科,还有迟迟没有过关的普通话,以及后来受到“仕途之风”的影响,走上了考公务员的道路,迫使着才掀起的写作狂潮在失意中随之淹没了。
我是在二〇一五年重返写作之路的,虽然开了一个好兆头,在一年的时间得以在《黔西南日报》上发文二十三篇,但是,其他刊物上的太多石沉大海,还是让我无比的心灰意冷,一遍遍问着自己,难道不是写作的料?当我与我的三哥道出了心里的苦闷,他开导着说:“万事开头难,只要持之以恒,就会有成功的一天。”我在半信半疑中又重新振作起来,义无反顾地徘徊在希望渺茫的文学路口。在这三年多的时间里,虽然有人带着几分戏谑的口吻开导我,说多跟编辑搞好关系,就不愁发文了,还煞有介事的举一些事例给我听。我的三哥听说了,笑着说哪有那样的事,只有凭真本领,才能发表真文章,走得更远的文章。一个个纸刊,或者一个个平台,就有着不同的编辑。我是一直跟他们打交道的,也是在跟他们打交道的过程中,遇到了帮我润笔后发文的编辑,打电话给我要我多作修改才投稿的编辑,直接拒绝我的文章的编辑……一位位编辑,就像一位位严师——不,就是一位位严师,站在我可仰望却又到达不了的地方。幸亏,越来越多的磨砺让我的韧性十足,不想这么容易退缩。
三年多的时间下来,我在不断努力学习的过程中,似乎迎来了人生的曙光,居然能在省级刊物《当代教育》发表两篇散文,《贵州民族报》和《劳动时报》各发表一篇散文,更加可喜的是,还在二〇一八年让文章陆续发表在国家级刊物《华夏散文》和《散文选刊》(下半月刊.原创版)上。我激动得哭了。“三年啊三年,我夜以继日的研究知名作家的文章,并笔耕不辍的坚持写,才盼来了今天啊!不,我还得感谢拒绝我的严师们,是他们以不得不展现在我面前的冷漠面孔,让我选择知难而上。”我也深知,摆在面前等着我要走的路还有多艰难,像《人民日报》、《人民文学》、《北京文学》等等刊物的编辑们,仍然像天山上的雪莲,盛开在我一时无法采摘的地方。但是,我不但不气馁,还感谢他们以如此的存在方式,让我充满了前进的动力。事实上,文学如此,教书亦然,都有严师的无处不在。是他们的所谓刁钻啊,才成就了我的人生。所以,我对跟我打交道的严师们,无论过去、现在,还是将来,都一直心存感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