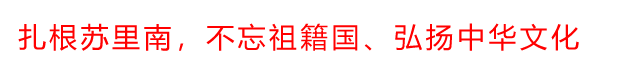苏里南印象之——天堂里的印迹(作者:刘庆丰)
| 发布时间:2018/8/14 | 来源:作者投稿 |
苏里南首都帕拉马里博有个叫新阿姆斯特丹的地方,美丽的如人间仙境,两条河在这里交汇入海,一条是苏里南河,另一条我不知名,却一样浩瀚。那里有个小渔村,恬静的如丹麦的童话。
一次偶然的机会,我去了那里,我没有想到她会那么美,美的不在我的意中,甚至这多年的梦里都没有如此美丽的地方。我不知怎么形容她,只好用梦幻吧——虽然我的梦幻里也没有过她。我想尽了形容词好像都不足以形容她的美,索性不费脑筋了,一个字,一句话,美,真的美。
起初我以为那是个玫瑰花般的地方,风流遍地,脂粉飘漫,似罂粟般让我欲罢不能。眼见后却是个茉莉花般的地方,洁净,淡雅,清香四溢又如幽兰淡淡的,让我心静如秋水,不起波澜,唉,是她的名字误导了我。以为依旧如阿姆斯特丹一样——欲望之都,粉红颜色。
阿姆斯特丹是荷兰首都,它一直是我心驰神往的地方,可惜一直无缘前往,那里的风流据说足以让天下所有的男人迷茫。虽然每次到苏里南都在那里转机,可是始终在机场内而已,阿姆斯特丹只在眼前——却也只在眼前。
所以苏里南的这个地方,就让我无限的向往了。
可是她却给了我另一种惊喜,那是我灵魂里向往的,我不敢触及的,胜过我的心思,我的神经。那是天堂,能安置灵魂的地方,我圣洁的梦。
遍野的安静令我忘却了的思想里的红粉,小小的村落迷失了我大城市的风光。她干净的有些不敢落脚,开阔的风都遥远。目之所及不见半点污秽,耳之所听没有一丝杂音。野草和鲜花,树木与飞鸟。噢,我的天堂。
还有那个小村庄,它并不出奇,那些房屋建筑也不是很特殊,可是围绕着的鲜花,只是这些鲜花就足以让人喜悦,花园里的梦,于我久矣。只是始终是他们的,于我无关。还是那句话我于天堂只是门外偶游,探头一望而已。
那些老旧的有些破败的江畔堤路,还有江畔发现的那些黑漆的对着入海口的铁炮。加上这里的安静。它斑驳了时光,这里又有了博物馆的味道。
我迷失在其中,漫步在四野。却又有让我意外的东西,几尊铁炮外,一块石碑让我迷茫了,铁炮何用?碑为谁立?石碑上的字令我惊讶了,惊讶之余有些哀伤。这是偶然的发现,我喜欢偶遇,可是这次却让我伤感甚至伤悲。
“一八五三年十月二十日,在这里被称为《新阿姆斯特丹堡垒》的地方,住有第一批来自中国的合同制工人。他们在这里建造了各式各样的种植场,从此这些华人开始在苏里南创业生根,此纪念碑于二零零八年献赠给苏里南人民”。
我大概可以猜到这是中国人立的,为了根,也为了未来,为了明白的活着,为了纪念。
我不知道第一批有多少人,他们从那里来。但是“合同制工人”,那是劳工,签了契约的劳工。还有那个年代正是中国百年耻辱的开始,国衰民弱,国耻民辱,国乱民逃。有家难顾,有国难安。四海漂泊,寄人篱下,卖力为生,以维家族。这轻描淡写之中包含了多少血汗泪水在里面,只有天知道了。
那次回来后,追溯了一下历史。史记第一批华人是从印尼过来的,十八个人,在海上漂泊了三个多月,其中四个人把生命留在了旅途上。合同到期后十一个人存活下来,其中八人返回了印尼,留下了三个人,成为苏里南华人的先驱,把根植在了这里。
我常常的想这十八个人一定是身体健壮,有冒险精神之人,可是却有四人为此付出生命在旅途上,可见旅途之凶险,它一定不是像泰坦尼克号那样悠闲。三个人死在苏里南的土地上,可见环境之不妥。唉,人之等级,劳工稍胜于奴隶吧。如此不易的旅途,却又有八人返回,吃尽千辛万苦,冒着丢掉性命的危险,来了却又走了,不留在这里,可见当时这里环境之恶劣吧。
我也不知道那个时代,这里什么样,如此安静吗?还是荒芜旷野,人烟渺却。但是草茂林丰,野兽横行,蚊虫肆虐却是一定,像我们现在住在首都郊区,都时常有野兽出没,蚊虫猖獗,一百多年前的远郊入海口想来更是如此。还有那些炮台却又显示这里曾经不安宁。我不知道两河所入是不是加勒比海,但是苏里南确是加勒比海国家,曾经的海盗闻名遐迩,这些对着海口的老炮似乎验证那些传言。
于是在那些蚊虫肆意,野兽出没,海盗横行的年代,在森林野草之中,我们的前辈是如何度过那些漫长的夜。这些念头让我难安。
这天堂般的地方,曾经是前辈们安身创业的地方!那时如此美丽吗?那是一百五十多年前的事了,一百多年后这里依旧寂静如野,小渔村的人气也抵不过自然旷广。一百多年前可想而知,如何的荒凉了。是他们开始了种植,开荒劈地。并且引导着一批又一批的同胞漂洋过海,落地生根。从最初的华工,变成苏里南的主人。一百多年这里的变迁有他们的奉献,青春,汗水,生命。
大西洋的风阵阵的吹过,码头上泊着几条渔船,岸边有渔夫编织着渔网。几个孩子在路口玩耍,是如此的安宁,祥和。这一切已经把曾经的历史淹没,如雨过天晴般。
蓝天,白云之下,两河交汇之处,一片瀚海之畔。我静静的站着,身后的野草在小丘上散漫,在微风中摇曳,几座红色的木桥连接着小丘边的水塘,灵动,飘逸如美女身上的腰带,小丘上几座木楼白柱,白栏,紫框,绿瓦,细瘦,苗条的如女模的腰身,却空无一人。我的面前,两河的水汇成的水势,胜过汪洋的海,以至于蓝天白云都不足以冲淡这水的白波,河对岸远远的两堵绿围更显这水势惊心。那些铸就的铁炮又让这里有沧桑的历史之感。这是画里的世界,野性与温柔,悠远与咫尺,澎湃与舒润,这一切浪漫了我的情怀,我失却了来时的欲望,却起了执手的温柔,在这红桥上,小楼内,听风语,待雨袭,望云飞,伴月行,泛舟月夜,坐拥霞佩。我羡慕起这小丘后小村里的人,眼红他们的日子,这是我心中渴望的地方,却可望不可及,还有我渴望这里,这里有前辈走过的足迹,于我就不陌生了。
我殷殷的渴望,却依旧不可及。我只好把她封存,当做一次梦,藏在心里。
这是我上一次来,游荡到这里,一次偶遇心里的波澜。
这一次来苏里南快三年了却再无缘到此。一八年是华人到此一百六十五周年了,那当是个大日子,苏里南的各届华人开始准备纪念活动了,它勾起了我上一次到此的回忆,我不知道那些前辈是否埋骨于此,那里隔着大西洋,那头却不是故里。可是他们并不孤单,因为后来者没有忘记他们。他们或许没有想到他们努力的结果,只是为了生存。但是他们打开了一个新世界的大门,给了很多华人闯荡世界的启示,指引了方向,他们是先驱,值得我们怀念,感激。正因为有他们以及一代一代的华人的努力,才会有今天的局面。今日苏里南华人的昌盛始于他们。我们纪念他们,为他们树碑立传,存留人间。也是告知后来者源头所在,根在那里,并告知世人,所有做出贡献者都不会被忘记。即使没有碑,他们依旧在人心里,胜过一切,永不消逝。
一八年八月于苏里南
附上一份名单是十八位先驱的名字,以告慰他们没有被遗忘。他们是:邓炳(煮糖工,这批劳工的工头)、苏德学(种蔗工)苏德修(种蔗工)、陈甫华(种蔗工)、陈士元(于1853年8月9日死于船上)、陈德励(种蔗工)、陈忠(煮糖工)、周安群(于1853年9月19日死于船上)、周在(抵岸时以患病,需送医院救治)、何俊杰(1853年10月十七日死于船上)、叶律军(种蔗工)、叶炳(种蔗工)、林德瑞(种蔗工)、卢蔼(种蔗工)、刘琻(种蔗工)、魏亜牛(煮糖工)、魏金胜(种蔗工)、欧杰(1853年7月18日死于船上)。首批华工于合约期满只有十一人存活,其中八人返回印尼,三位自愿留下,受聘于政府担任下批华工翻译,此三位便成为苏里南华人的先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