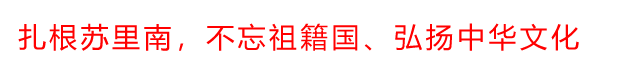心尖上的母亲茶 (作者:杨启彦)
| 发布时间:2018/6/13 | 来源:作者投稿 |
我家茶几上,摆着滇红、普洱、铁观音、大红袍等名品。它们包装精致,熠熠闪耀。朋友临门,品茗闲话,可为一乐。在这些贵族的旁边,还有一个玻璃罐子,里面装着粗糙的茶叶。它无名无姓,不入雅流,可它是我的宝贝。
我工作地在乡下小县城,生活有些单调。空余,我就到四周的茶园闲逛,看看有没有废弃的茶地。后来,我在离县城六七公里的地方找到它。那废茶园在一个小山的顶部,满是杂树杂草,但有茶园陈迹。我共发现了二十几株茶树,都掩藏在松树和杂木林中,有的比人高,有的盘着身子趴在地上。过了些天,我带了砍刀上山,把高的茶树砍矮,把拦着太阳的杂树枝去掉。这样,它明年就会发出嫩生生的新枝来。所有工作做完了,我四仰八叉地躺地如茵的草地上,蓝天渺远,白云去来,轻风拂面,吹起衣襟。
小时候,父亲在外地工作,母亲带着我们姐妹五个,日子过得很清苦。每到清明前,母亲总会抽出一点时间,带我们到村后的山上一处荒废的茶园采野茶。我总觉得很无趣,并不十分用心。母亲就不同,她有时跪在地上,盯着茶树,像绣花一样。她说怕采了大叶子,又怕掐了嫩芽;她有时轻轻地翻动茶树,去寻那毛绒绒的一叶;有时轻轻地拂去枝叶间的蛛网,拍落小虫。对这些,我颇为反感,觉得跟她采茶也不相干——又不是她的菜园子。回家后,把茶摊匀在筛子里晾着,夜间端到野外露天下,她说这是露茶。待茶全蔫了,再用木甑蒸,就像蒸包子一样。待蒸至半熟,又放到筛子里,趁着微温,用手揉搓。这时片片嫩叶便蜷缩为一团了。揉搓完了,便又是晾晒……茶制做好了。母亲把新茶装进一个不透明的大瓶子里,那是父亲拿回来的装凡士林的药瓶子,壁厚不透光。母亲看着泡出来的茶汤,绿中微黄,非常开心。说这茶开胃消食,喝了顿有精神。那时我觉得这茶很苦,不如白糖水好喝。
离清明节还有好几天,我就驱车上山了。阳春三月,惠风和畅,山顶上美不胜收。我提着小桶,遍地去找嫩绿的茶芽,毛绒绒绿莹莹的,正眨着眼睛盼望我来呢。我像母亲一样,一会站着,一会蹲着,小心翼翼地掐茶,像伸手去抱初生的婴儿。我不漏过每一个茶尖,不多采一个大叶。我像母亲一样,每采完一株,我都细心把茶树身下的杂草拨掉,把压着它的杂树枝砍掉。野茶树还没有采完,小桶就满了。我躺在山上的草坪上,蓝天茫远,孤云独去,正像母亲的身影……
那时,我认为因为家穷,没钱买茶叶,才去采野茶。客人品后都说好,我总觉得很苦很涩。老爸酷爱这茶,不轻易给别人喝。那个装凡士林的大瓶,现在这瓶子就放在我的茶几上,暗淡无光。如果说龙井是清香的玫瑰花,它就是浓烈的八月桂;如果说铁观音是初春的梨花,它就是秋天的黄菊;如果说黄山毛峰是清淡的鲢鱼,它就是淳厚的宣威腊火腿。从这浓酽中,我品出了人生五味,品出了母亲的味道。